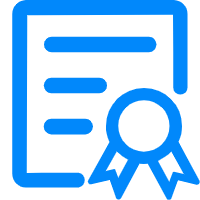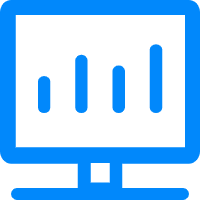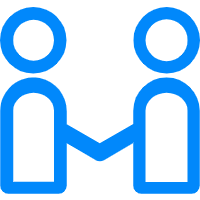2024年冬,国企某设备采购部经理陈明被公安机关带走,罪名是涉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举报材料显示,陈明在任职期间,其妻子注册了一家与国企经营范围相同的贸易公司,两年内承接了3笔国企潜在客户的业务,涉案金额达230万元。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陈明利用职务便利为妻子公司牟利,建议量刑3-5年。辩护律师赵毅会见时,陈明一脸委屈:“我妻子开公司的事我早就报备了,那些客户是主动找她合作的,我从来没利用过职务资源!”
证据深挖:厘清“职务便利”与“独立经营”的界限
赵毅团队首先聚焦“职务便利”的认定。他们调取了陈明的任职文件和国企的客户管理制度,发现陈明的职权范围仅限于设备采购审批,不负责市场开拓和客户维护;其妻子公司的3笔业务中,有2笔客户是通过行业展会自行联系,1笔是经第三方中介介绍,均无证据显示陈明参与其中。更关键的是,陈明在妻子公司注册时,已向国企纪检部门提交了家属从业情况报备表,明确载明公司经营范围。
根据《刑法》第165条,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要求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赵毅意识到,本案的核心在于区分“家属独立经营”与“利用职务牟利”。他向检察机关提交了展会参展记录、中介合同、纪检报备材料等证据,主张陈明既未利用职务信息,也未干预客户选择,其妻子公司的经营活动具有独立性,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法律博弈:界定“同业竞争”与“刑事犯罪”的边界
审查起诉阶段,控辩双方围绕“家属经营同类业务是否必然构成共犯”展开辩论。检察机关认为,陈明作为国企高管,对家属经营同类业务负有监管义务,其放任行为已构成间接故意。赵然则反驳称,法律并未禁止国企人员家属从事同类行业,只要行为人未利用职务便利,就不应认定为犯罪。他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强调“职务便利需体现为具体的职权干预或信息泄露”。
为增强辩护效果,赵毅申请调取了国企的客户流失分析报告,显示3家客户选择陈明妻子公司的原因是“报价低15%”“交货周期短”,与陈明的职务行为无关;同时,他邀请企业管理专家出庭作证,证实同类行业中家属独立经营的普遍性及合法性边界。这些材料进一步佐证了案件的非罪属性。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发布的国企人员犯罪典型案例指出,对于家属经营同类业务的案件,需严格区分“个人行为”与“职务行为”,避免简单以“身份关联”认定犯罪。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对同类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比例达28%,多数因缺乏“利用职务便利”的直接证据。
合规整改:辩护中的企业治理与风险防范
赵毅在辩护过程中发现,涉案国企的家属从业报备制度存在漏洞,未明确后续监管措施。他主动向国企提出合规建议,协助完善了《关联经营管理办法》,要求员工定期报告家属经营动态,建立客户资源隔离机制。这些建议得到了国企管理层的认可,也让检察机关看到了案件背后的制度完善空间。
最终,检察机关综合全案证据,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陈明利用职务便利经营同类营业,作出不起诉决定。案件结束后,陈明感慨道:“这次经历让我明白,职场中不仅要廉洁自律,更要厘清法律边界,主动合规报备太重要了。”
这起案件的辩护实践,展现了刑事辩护在国企人员犯罪案件中的独特价值。当职场行为与刑事风险交织时,辩护律师不仅要精准运用法律条文辨析罪与非罪,更要深入分析案件背后的企业管理制度问题。通过细致的证据核查、严谨的法律论证以及积极的合规建议,让司法裁判既坚守法律底线,又推动企业治理完善,这正是新时代刑事辩护维护公平正义的多元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