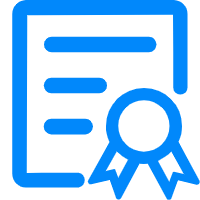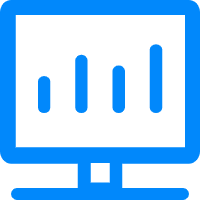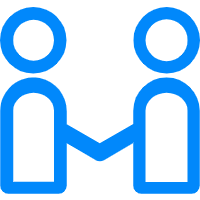2024年夏,苏州某连锁超市店长王芳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情源于一次市场监管部门抽查:超市销售的某知名品牌洗衣液被鉴定为假货,涉案金额达12万元。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王芳作为店长,明知是假冒商品仍予以销售,建议量刑1-2年。辩护律师刘畅会见时,王芳焦急地说:“这批货是通过正规经销商进的,有完整的进货单据,我真不知道是假货!”
货源溯源:区分“明知销售”与“被蒙骗”的关键
刘畅团队首先将工作重点放在货源渠道的核查上。他们调取了超市的进货合同、付款凭证和物流记录,发现这批洗衣液来自一家持有品牌授权委托书的经销商。进一步调查显示,该经销商的授权委托书系伪造,但王芳在进货时已核实了经销商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资质文件,且此前与该经销商有过多次合法交易记录。更关键的是,假冒洗衣液的包装、防伪标识与正品高度相似,普通消费者乃至超市工作人员难以通过肉眼辨别。
根据《刑法》第214条及相关司法解释,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要求行为人“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销售”。刘畅意识到,本案的核心在于王芳是否具备“明知”的主观故意。她向检察机关提交了进货资质文件、过往交易记录、假货鉴定对比报告等证据,主张王芳已尽到合理的进货审查义务,其销售行为系因经销商欺诈导致,主观上无犯罪故意。
金额争议:厘清“销售金额”与“货值金额”的边界
审查起诉阶段,控辩双方围绕涉案金额的认定产生分歧。检察机关以12万元的进货总价作为“销售金额”提出指控。刘畅则反驳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销售金额”是指实际销售出去的商品金额,本案中超市仅销售了3万元的假冒洗衣液,剩余9万元货物尚未售出,应认定为“货值金额”且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
为增强辩护效果,刘畅申请超市的财务人员出庭作证,出示了详细的销售台账和收银记录,证实假冒洗衣液的实际销售情况;同时,她提交了市场监管部门的现场查封清单,证明剩余货物未流入市场。这些证据清晰区分了“已售”与“未售”金额,为降低案件情节严重程度提供了有力支撑。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报告显示,在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件中,因“主观不明知”或“涉案金额认定争议”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占比达29%。司法实践中,对销售终端从业者的主观故意认定需结合其认知能力、进货渠道、价格差异等综合判断,避免客观归罪。
合规整改:从案件辩护到行业风险防范
刘畅在辩护过程中发现,该连锁超市缺乏完善的进货查验制度,对供应商资质的审核流于形式。她主动向超市总部提出合规建议,协助建立了“供应商资质三重审核机制”,要求对品牌授权文件进行官网验证,对批次商品进行抽样送检,并引入假货责任险。这些措施不仅得到了超市的采纳,还被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作为行业规范案例推广。
最终,检察机关综合全案证据,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王芳具有销售假冒商品的主观故意,且实际销售金额未达“数额较大”标准,作出不起诉决定。案件结束后,王芳在超市内设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栏”,感慨道:“以前觉得进货只要有单据就行,现在才知道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法律风险就藏在货架的每一件商品里。”
这起案件的辩护实践,展现了刑事辩护在民生领域知识产权案件中的独特价值。当终端销售者面临刑事指控时,辩护律师不仅要精准运用法律条文辨析罪与非罪,更要深入挖掘案件背后的行业管理问题。通过细致的货源核查、严谨的金额认定以及积极的合规整改建议,让司法裁判既坚守法律底线,又兼顾市场实际,这正是刑事辩护维护公平正义与市场秩序的生动体现。